第94次马哲论坛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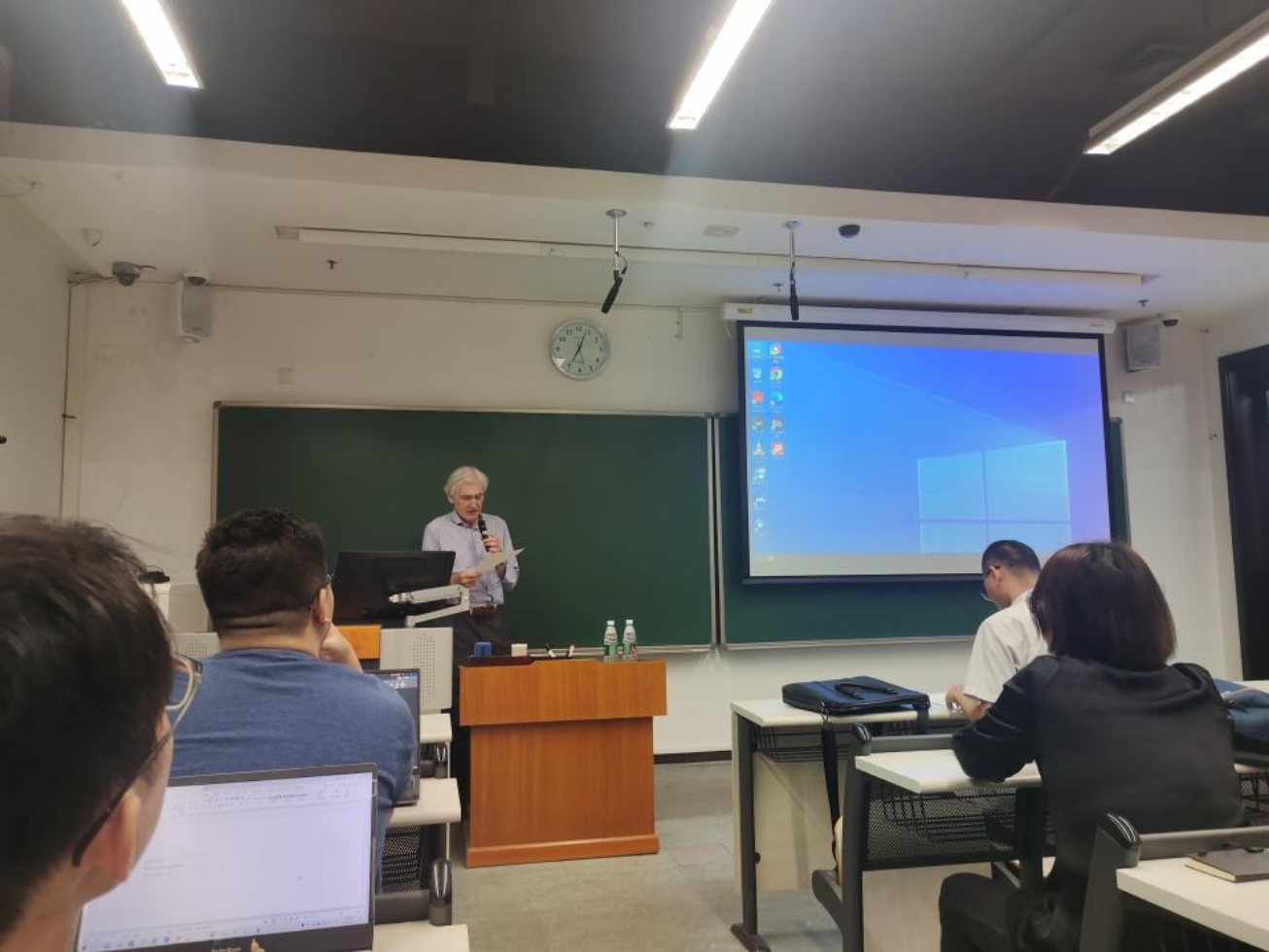
9月15日晚七点,来自伍伯塔尔大学的斯迈尔·拉佩奇(Smail Rapic)教授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为同学们带来题为“论哈贝马斯在《这亦是一部哲学史》中将哲学作为一种‘自我理解’——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阿佩尔的话语理论为背景”的线下讲座。
拉佩奇教授讲到,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提出规范性的世界历史发展逻辑理论,这一理论面临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逻辑既不能等同于超时空的理性目的论,也不能立足于偶然的事实,因为前者将导致历史哲学的教条主义,后者意味着放弃对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的假设。因此,规范性发展逻辑的有效性何在就成为哈贝马斯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晚近的作品《这亦是一部哲学史》中,哈贝马斯重新启用一度被怀疑和悬置的对种群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但是削弱了将其从社会强制语境中抽离出来的主张,并且强调了哲学作为一种世界和自我理解过程的理性批判特征。其中,“自我理解”这一概念来自马克思对于批判哲学的定义,即“现时代的斗争和欲望所要获得的自我理解”,但是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针对的是社会理论问题,而在哈贝马斯书中特别针对一种区别于科学主义的哲学反思。
阿佩尔(Karl-Otto Apel)支持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和对种群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方法,但是他不认为应该像哈贝马斯在《这亦是一部哲学史》中一样将种群历史的规范性发展逻辑还原为经验上可呈现的内容,比如“法律制度、法学程序以及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实践”等社会中可观察到的道德学习过程。阿佩尔解决哈贝马斯所遭遇的“规范性发展逻辑的有效性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提出这样一个论断:话语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设定(posit)”并“预设(presuppose)”了种群历史中规范性进步的“准目的(quasi-telos)”。
话语伦理学的观点来自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启发,旨在讨论对话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预设性共识。阿佩尔在《超验实用主义——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中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不使用超验形而上学概念的情况下建立理性可理解的“对人类实践的自我反思”和“历史重建”之间的联系。阿佩尔仅仅在包含理论知识的层面上使用“实践”这一概念,他认为马克思同样也将理论知识作为一种实践形式,但是正统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阿佩尔想借用皮尔斯的超验实用主义变革给“实践”观点一个充分的形式。超验实用主义是指在寻找真理的交流过程中,对话者所需要的对真理标准的规范描述。皮尔斯将“真知识”定义为在共同体中对日常共识形式的观念,知识过程是一种集体实践。因此阿佩尔认为,“共识”作为论证话语的隐含前提是“哲学反思不可避免的出发点”。在他的超验实用主义中,理解过程的前定设置(presuppositions of understanding-processes)就如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一样,成为使得客观经验认知得以可能的主观条件。
拉佩奇教授试图运用阿佩尔的“超验实用主义”理论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作为世界和自我理解过程”的概念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虽然阿佩尔本人并未使用“自我理解”这一概念,但是他所使用的黑格尔的“绝对反思(absolute reflection)”概念,有助于建立哈贝马斯的“理性与自我理解”和马克思唯物史观之间的联系。黑格尔的绝对自我反思结构,克服了康德既无法将超验主体放置在现象界又无法归于不能被认识的本体界的困境,提出一切直接给定的东西都应看作是被设定的,同时又必须把这些设定的东西作为前提。黑格尔将“作为前提的设定(positing as presupposing)”这一反思逻辑图式应用于理解精神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哲学与对象的关系。这意味着,一方面,人类精神作为一种它无法支配的力量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自我认识必须包括它从自然中的进化;另一方面,自然又被人类精神所“设定”,因为任何可以归因于自然的决定性都是建立在范畴框架之上的。通过对黑格尔的绝对反思结构进行后形而上学的重新表述,阿佩尔提出了自我找回原则(self-retrieval principle),这一原则所具有的反思逻辑结构可以转化到马克思对批判哲学所具有的自我理解特性的定义中。即,批判哲学要从现存现实所特有的形式出发,把发展真正的现实作为自己的义务和最终目标。因此自我找回原则要求:超验实用主义和话语伦理既是设定的又是预设的, 并且关于两者的认知必须被设定为历史进步的准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和思维起源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体现了他们对“自我理解”过程的认识,说明了只有当人们知道历史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也就是知道历史的结构性原则时,人们才能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力图从理论上洞察历史进程的结构性原则,而这些原则将导致对当前社会条件变革可能性的自我理解。如果对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可能性范围认识不足,人们就会把社会活动“固化”为“凌驾于我们之上的物质力量”,导致自我理解的动摇。
虽然哈贝马斯跟马恩一样也把人看做处于文化学习高级阶段的理性动物,但是他不认同马恩仅仅用“劳动”定义人类种群的理解。哈贝马斯在《这亦是一部哲学史》中同时从“参与者视角”和“观察者视角”来解读“历史中的理性的轨迹”。在古老仪式刚产生的时期,人们只是专注于参与共同仪式的行动,而未以叙事的形式掌握仪式的命题内容,也没有形成集体意识;到神话产生的时期,神话内容的语言化和法典化逐渐取代了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体现出系统功能观察者对其集体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自我理解,并且有了区别于主客二元的第三人称视角,系统功能观察者的视角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国家社会形成之后,自我理解通过法律规范体现出来。不同于自然而然构成的部落,国家和政治是在轴心时代出现的形而上学和高级宗教的影响下自愿、有意识地形成的,首次体现出了组织社会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哈贝马斯认为“自我理解”的概念开始于种群历史从古老仪式到神话世界观的转化,即,神话所体现出仪式的自在的自为性(the being-for-itself of the in-itself)开启了自我理解的进程。拉佩奇教授认为哈贝马斯对种群历史合理化过程的重构具有阿佩尔意义上的绝对反思结构。这是因为,神话世界观启动了一个学习过程,它使社会行动者自觉地形成自己的生活条件,同时考虑到系统性要求,也使他们意识到普遍规范的有效性要求。这意味着由神话世界观开启的学习过程,奠定了轴心时代以来的“系统适应”加“内生学习过程”的双重进路,即在自我设定认知的同时又预设既成的认知。因此,拉佩奇教授认为阿佩尔可以保留规范性的发展逻辑概念在种群历史中的理论主张,并且避免哈贝马斯在《这亦是一部哲学史》中将发展逻辑降低为描述性内容的让步。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踊跃提问,与拉佩奇教授就以下问题展开讨论:1. 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对交往和实践的关系的理解;2. 哈贝马斯的历史演进逻辑理论作为相信历史进步的谱系学,是否会受到权力等因素的干扰而遭遇削弱和质疑;3. 哈贝马斯将自然历史作为自我理解的历史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可以把人类行动简化为智力活动或主体间互动,而不考虑到身体和物质的作用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4. 激情、欲望、斗争在革命行动中的地位是否被哈贝马斯忽视;5. 阿佩尔的话语伦理概念的定义及其与超验实用主义的关系;6. 设定与预设概念的关系;7. 《这亦是一部哲学史》的发表是否可以促进哈贝马斯式对德国传统哲学的解读与安格鲁萨克逊式的解读之间的融合;8. 系统性理性的含义及哈贝马斯为何认为它应该被限制;9. 若理性扩张具有自我指涉性质,即可以自行产生前进的资源和动力,这一理性扩张的动力是启蒙的或世俗的?; 10. 西方对概念合理性的论证策略虽然经历了从先验信念到到仅仅依靠理性和自我反思的变化,但是其前提还是依赖于一些主导性的先验世界观,中国哲学则没有这种主导型的先验世界观,那么中国哲学中是否有自我反思性的理念,这种差异是否会导致中国式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的不同;11. 哈贝马斯将哲学的历史解释为人类种群实现自治的发展历史,并主要阐述理性过程和逻辑发展历程,是否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而更接近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发展史。
供稿:祁玥
供图:田竞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