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究病毒之理,当有扶社稷之心
来源:
作者:
时间:2020-03-20
本文作者:周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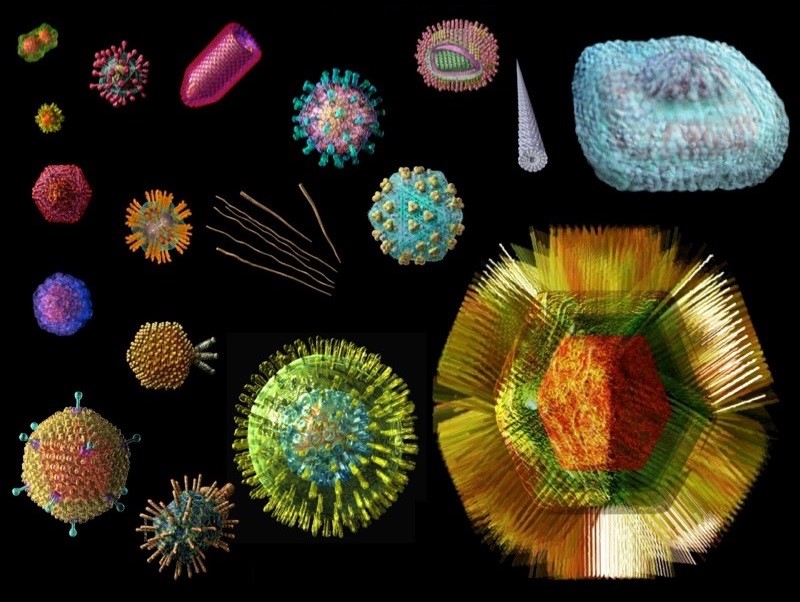
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决定着科学家们认识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就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而言,科学共同体内部对其命名、分类与防治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非常正常。
实际上,在不可能做大量的重复实验或不可能进行充分质疑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对新鲜事物的理解与预判难免会出现失误。历史是帮助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情境性和科学家的局限性的最好教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提出的细菌致病学说如日中天。受该学说的启迪,德国农业化学家麦尔发现烟草花叶病是一种植物传染病,但囿于当时的研究条件,他未能证明烟草花叶病的致病因子是一种滤过性病原体。
首先用实验证明烟草花叶病的致病因子是一种滤过性病原体的,是俄国植物生理学家伊万诺夫斯基。但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滤过性病原体是一种有别于细菌的新型病原体,因此没有及时对滤过性病原体进行深究。
由于传染病皆由细菌或其毒素引起的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同,因此当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新型病原体——口蹄疫病毒被“发现”之后,德国的微生物学家吕夫勒和菲洛施等人仍然不愿意抛弃主要由其师长科赫提出的既有理论,继续将这种新型病原体视作一种“极小生物”。
虽然荷兰的细菌学家贝杰林克改造了传统的“病毒”概念,并赋予其全新的涵义——“传染性活流质”,但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这一新观念,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人们很难想象非颗粒形态的流质也像单细胞细菌那样具有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贝杰林克大胆提出的“病毒”概念遭到伊万诺夫斯基等人的批判也就在所难免。
一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植物病理学拓荒者杜加尔基于一系列实验研究将“病毒”的概念发展成为可在细胞内自我增殖的亚微观颗粒,但他既没有看到这种颗粒形态的病毒,也不知道其本质究竟是什么。
因此,当美国生物化学家斯坦利借助当时最先进的酶蛋白质结晶技术于1935年制得烟草花叶病毒结晶,并指出“病毒”是一种蛋白质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议,因为这种“病毒”概念颠覆了很多人对生命和物质的认知。自我增殖被认为是只有生命才具有的属性,如果作为化学物质的蛋白质确实具有这种属性,那么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在哪里?生命究竟是什么?
对斯坦利的研究结论表示怀疑的人有很多,但很快就用事实修正其研究结论的唯有英国的鲍登和皮里。鲍登和皮里1936年用详实的实验数据证明,烟草花叶病毒中除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外,还含有少量的RNA,只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RNA才是病毒的遗传物质。鲍登和皮里还从这种核酸蛋白质复合体具有各向异性推出,烟草花叶病毒应该是杆状颗粒,而不是球状颗粒。
在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人、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斯特·鲁斯卡的弟弟哈尔墨特·鲁斯卡的协助下,德国生物化学家考舍于1939年终于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了烟草花叶病毒,并确认其为杆状颗粒。不过,考舍给出的烟草花叶病毒的大小尺寸并不准确。
从最初断定烟草花叶病毒为滤过性病原体,至最终直接观察到这种滤过性病原体为一种亚微观颗粒,人类整整用了41年。在这段时间里,很多科学家都为人类加深对病毒本质的理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这批跨时代、跨国别、跨专业科学家持续性的、反思性的“集体学习”,第一株病毒是不可能这么早就被人类发现的。
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家们虽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出了一些符合事实的、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论文或报告中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简言之,没有一篇论文或报告没有错误,没有一位科学家的见解完全正确。至于没有为加深对病毒的理解作出贡献,甚至对病毒概念的形成产生严重误导的论文或报告则不计其数。
如果当时的人们对这些论文或报告推崇备至,甚至将这些论文或报告的作者奉若神明,不仅不利于病毒概念的形塑,甚至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倘若历史上的绝大多数论文与报告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错误,每一位科学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那么今人该如何看待科学认知,如何对待科学家?尤其是,今天的科学家会不会像100年前的科学家那样,即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也会频频出错?如果会,那么科学家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要不要更加谦虚,在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时要不要更加谨慎?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味地迷信科学和盲从科学家并不能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也无助于解决时代赋予我们的诸多科技难题。怀疑的世界真理多,盲信的社会谬误多!科学始于疑问,过去是如此,现在恐怕也是这样。
通过回顾烟草花叶病毒的发现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是累积性的,很多重大发现都是由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换言之,仅靠少数明星科学家的艰辛付出是不可能将科学大厦建成的,更何况明星科学家往往也是在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筛选中被逐渐识别出来的。
因此,有必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机制。
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建立平等对话的机制,才有可能使每一位科学家的真知灼见都不至于被埋没,同时确保任何权威的认知盲点都不至于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真理越辩越明,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批评错误观点和理论的方法不是压制这种观点和理论的传播,而是提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观点和理论。
要建立合作交流的长效机制,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大家都能理解的话语体系,不能各说各话;其次需要搭建一批方便各国学者高效沟通的平台,不能画地为牢。
可以说,无论是德国学者、俄国学者,还是美国学者、英国学者,如果大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毒过程中,不是基于普遍主义立场行动,就不可能建立起那么庞大的“行动者网络”,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那么强大的如实表征病毒本质的能力。
这次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过程中,不同的科学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的为了解生灵于倒悬,置个人安危荣辱于度外,实事求是,直言真相;有的为了帽子、位子和票子,顶着科学权威的光环,无视事实,糊弄上下;有的急于将所学业务专长回报社会,主动请缨逆行,上善若水,救死扶伤;有的急于将各地收集的民众患病数据用于发表学术论文,沽名钓誉,罔顾使命;有的为了解明病毒机理在实验室连续奋战,小心求证,循序渐进;有的则将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初步结论拿出来炒作,夸大其词,误导民众。
痛定思痛,铭记科学研究具有局限性和科学知识具有情境性,支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机制,也许是科学家们,尤其是带有“帽子”、担任着重任的领军科学家们最应该做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每个科学家对建立健全的科学文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主要内容已于2020年2月27日刊发在《中国科学报》第1版。)

周程,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交叉科学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室)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
兼任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科技与人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科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科学技术方法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曾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非常勤讲师(主讲“科学史演習”课程),早稻田大学留学中心客座准教授(主讲“中国研究の最前線”课程),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教学部主任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社会史,科学实践哲学,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
主要代表作有:1.《福澤諭吉と陳独秀:東アジア近代科学啓蒙思想の黎明》(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独立撰写);2.《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独立撰写);3.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主持撰写);4.《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主持翻译,[美]Toby E. Huff著);5.生命是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主持翻译,[奥]薛定谔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