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松:”黄昏永续——“虚假观察者”关于疫病的琐言
本文作者: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大约三四周之前,文研院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以我的观察,这些学者都是文研院气息的爱好者,这是一种很纯粹的喜欢,非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才是真正可爱的)发了一个倡议,希望我们就还在进行时中的疫情发表一些感想。
文研院的老师还特意叮嘱,“你应该有很多话说,毕竟你是做道教的。驱瘟避疫是你本行啊…”彼时我觉得有些无奈。道教研究学者应该会作法、应该能炼丹,这种玩笑中蕴含着强烈的常识压力,似乎也成为某种职业性的技能要求。这种压力一直让我很排斥承认自己是一个道教学者,而这样的排斥又常常被解读为看不起道教信仰。尴尬的两难就是一种日常。常识的压力就是一个人文领域里的职业学者有责任也有必要展示他的专业知识。通过某种快递式的知识把尘封在故纸堆里的过往以一种比附的方式呈现出来,牵连到某个当下的鲜活处境,进而让阅读者在“原来历史上这种事情也时常发生”的宽慰和“他们用如此原始和不科学的方式应对危机”的优越感中安然喝下完全无益也无害的知识饮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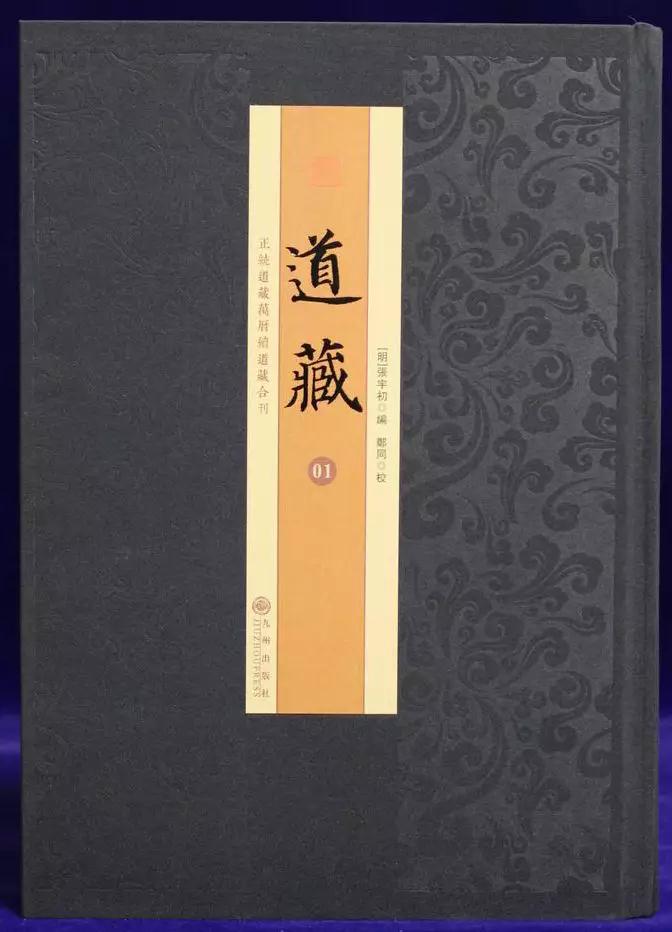
《道藏》书影
我想,作为一个道教学者,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从《道藏》里找到若干驱瘟的仪式文本及关于大疫治愈神迹的记述,得出不是结论的结论:其一,你看,虽然他们比我们落后那么多,但他们都挺过来,我们也能挺过来;其二,愚昧和落后的观念才是造成灾难的人为机制。这也是社会赋予一个职业学者的话语空间,正确的做法就是顺坡下驴地在话语空间里展开言说…
这样的姿势在我看来十分不真实。在人生最悠长宅家假期里,我一直在无法写作的焦虑中、与家里的小魔王斗智斗勇中、不停手地刷疫情数据中、乐此不疲地打听各种(越危言耸听越好的)小道消息中熬过日历里的每一张纸片。在这样的真实经验中,真正无可抵抗的就是“日常”的统治力,我们那么拒斥当下持续了几十天的“假期”的“日常”,我看到了日常之间战争,以及高度秩序化的混沌。“不真实”的感受让当下的“真实”成了敌人,我们通过不断回向日常秩序的方式对抗当下的“日常”。正像一个在森林里迷路了的人,森林的风景是完全不可见的,不断涌来的就是迷失的惶恐和因此产生的懊恼的自责。
最近一个多月,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景观就是,疫病给了所有人话语生产的良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话语生产与观念交叠对抗“非日常”的焦虑和恐慌。这些话语生产的基本形态过于复杂,一个可能的共通之处就是所有说话者都是虚假的观察者,自以为是的局外人。在一个概莫能外的社会危机中,保持观察者的视角展开言说是逃离焦虑的好方法。于我本人而言,尽量保持不与这种“异常的日常”对抗的心态并且小心地不加入话语填充物(Discourse Landfill)生产的狂欢是应有之义。
昨天(3月18日)听到渠敬东教授在视频中提及涂尔干关于社会密度和传染性社会的论述,蓦然意识到最具有传染性的不就是说话的欲望和虚假观察者的视角吗?置身其中又超然于外的悖谬一直是所有知识人不能逃脱的宿命。进而开始怀疑,保持不与“异常的日常”对抗的心态是否也是矫情?如果是,那么就尝试放下抵抗,感受一下反思异常的“日常”。于是就有了以下的Landfill(鄙人十分喜欢这个词,就是填充物,几乎没有什么用,而妙处就在于“几乎”):
毫无疑问,这个春节假期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奇特的,它长得出奇,也压抑得出奇。假期与疫病的迭加让隐约的恐惧和难免于难的担忧被放大了很多,我们又没有办法用忙碌抵抗它们。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与恐惧和担忧平和相处的能力。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被日常秩序驯化了,只能活在“实际的”抑或“被想象出来”的高度秩序化了的日常里。真正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无序与庸常。

2月1日,北京西站出站口
我们为什么盼望假期呢?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包含着一种典型的吊诡:高度重复的日常必须时常被假期打断,以避免把人们抛入庸常的疲役之中。假期的安排是日常秩序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功能就是打断它,并且以此保证日常秩序以可中断且可恢复的方式持续下去。同时,我们的日常秩序只有在被中断的时候才被显现出来,才可以被观察和分析。退而言之,即使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活在一种想象出来的秩序之中的。毕竟在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节奏中,每一个个体的丰富性和经验的偶然性虽然可以被忽视,但终究不能被消灭。
如果说被中断的日常秩序就是我们盼望的假期,那么太长的假期又让我们对日常性的统治力有了充分的认知。疫病期间自觉减少出门,职业社会的日常秩序的核心——工作——几乎停摆,那些曾经毫无余隙地包裹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我们突然看到了日常秩序像黑洞一样强大的席卷能力。一旦日常秩序这个黑洞停止运转,时间就以很缓慢地方式压垮了每一个人的耐受力,闲得发慌就很直白地表达了“悠闲的限度”。
过往的数十天,在两种日常模式之间进行剧烈且不合预期的转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我们不得不处在“何以丧失日常进入无序”的不断省察和“何时回到日常秩序”的持续焦虑之中。这种焦虑既有面向过去的省察,也有面向未来的猜测。在被迫的无所事事和用以抵抗“虚假悠闲”的没事找事儿中,我们可以尽情地放纵自己的焦虑和烦闷情绪。更要命的是,这些情绪被持续放置在我们意识领域的焦点位置上,不断放大,直至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公共“症状”。确实的状态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知道”。由此,持续且充满矛盾的信息与各种被知识和权威包装过了的话语就成了真正的刚需,我们自觉地被席卷到不断被生产出来的话语和相互矛盾的信息之中,用信息的焦虑抵抗秩序的焦虑。

1月24日,戴口罩迎接鼠年的市民们
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最根底的认知挑战:长期被灌输的、关于科学与世界秩序的信念,不得不在无序的信息与话语的映照下反复被质疑。扑面涌来的信息和话语都有一个预设,它们的使命是揭示真实、传递客观。它们尝试说服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一切仍然在知识的秩序内,所有的无序只是来自暂时的未知。以此在智识的秩序重建中抵抗未知的、现实的风险与恐惧,制造一种有趣且脆弱的印象——因为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所以我们能够掌控它。此外,就社会信息的生产和分发机制而言,我们会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信息渠道和内容似乎都是指向秩序的,然而他们被选取和理解的过程却是完全无序的。不妨说,我们活在一个高度混沌的信息布朗运动之中。与此相对,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这些高度混乱且缺乏真实性判定的信息又必须被秩序化,并且整合进一个丰富但划一的世界认识之中去。
最近的四十天,我身边最活跃的信息源就是中学的一个校友群。分布在天南海北、国内海外的,都被疫情中断了日常生活和职业节奏的数十人不断在群里以各种姿态发布信息并进行评论,我自己也十分严肃地上传过好几条已经被辟谣的所谓新闻。严格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信息混沌中的孤岛,我们首先想要得到的不是真实,而是确信和秩序感。秩序感的需求与怀疑的本能成了内心交战的双方。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显然不是日常话语和公共知识,而是一些不明觉厉、不知就里的术语堆砌起来的“专业表述”。谈到疫情,你要不能说出免疫风暴、不能知晓某几个英文字母缩写出来的且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药物或者设备,那么你就是缺乏话语自信的。
不妨说,当代社会给人一种十分荒谬的在场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任何人可以充分利用有限但被打扮得十分真实的信息,辅以自己的脑补实力,假装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现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共情的能力,用情感的方式“体贴”地加入任何一个现场。与此相对,从理智意义上,我们又都是怀疑者和局外人,哪怕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同样遭到超然的审查和诘问。

2月1日,张贴抵制疫情谣言宣传标语的工作人员
复杂的在场感并不是解放了我们的理性认知能力,而是放飞了我们的想象力。在日常生活的秩序里,我们的想象力总是被理性和常识统治的,而在日常秩序缺位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就彻底告别了常识的压力,开始在谎言、事实与自我感受之间不断漂移。其合理性就是,断裂了的日常秩序让我们可以尽情地在想象中试验混乱的边界和无序的后果。只有在这个时候,所有在平时被嗤之以鼻的怪力乱神都被以可能性的名义占据了话语生产的某一个角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起来。
这时,知识人或者科学家们就会用他们用专业术语和知识壁垒构造出来的、具有权威的话语提示已经漂移的想象力回到论证的伦理要求上来。于是乎,辟谣成了重要的话头。就我个人而言,方方女士与张文宏大夫两个人共同构成了基础的想象力空间,情感性的表达和理性的知识成为过滤和质疑信息的两个端点。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往复之中把自己埋进关于真实性的焦虑和省察性的反思之中,抵抗“无序”带来的不知所以且不知何时终了的焦虑。
除了面相各异且难辨真假的信息之外,以省察的名义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话语生产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作为象征的“病”或“病人”。无序的“日常”让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人都有一种“病态”的直觉,于是,病的象征性意涵延伸成为最简易的话语生成方式。不仅有一些人病了,社会也病了,思想也病了。简言之,我们都是这个无序病症的共病者。
自觉的反思与省察通过不断指出此前被我们认为是“有序的世界”由于自满或无知而遮蔽了的,其中包含着的无序的风险,以此来生产对抗“无序”焦虑的诠释。如果关于事实的信息是为了说明“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那么反思性的话语则是为了应对“为什么”“会怎样”的问题。诠释并不是为了解决,而是为了平复焦虑。让人恍然大悟的诠释使得听者可以暂时进入“无序背后的有序”的安全区间之中,而这些诠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序与日常就潜藏着这些无序与混乱。质言之,我们不是真正指出了混乱的根源,而是尝试说明在进入混乱之间的日常中就包含了某种混乱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关于日常的定义将无序和混乱消解在更新的日常描述之中。在其中,此前遮蔽真实的日常的误解和偏见,成为无序的替罪羊,而我们重新安然地活在一种持续向完善秩序前进的感受之中。

诠释并不是为了解决,而是为了平复焦虑
大抵上,职业学术的时代,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学者就是负责信息生产和鉴别的,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职责就是用诠释的话语和省察的语气顽固地保卫日常,即使这种保卫方式就是不断地用诠释重构它。在一个无限放大的关于“疫病”的隐喻之中,如果我们都是病人,那么我们就同时都是病理学家。
不得不承认的是,津津乐道的病理分析与治疗方案之间的距离,是无穷远。
诠释就是终结处,而不是行动的起点,这就是绝大多数公众对于反思性诠释缺乏信任和尊重的根本原因。诠释总是要直面诠释者们共同建筑的巨大障碍,即理性设定的所有人都拥有的怀疑能力和责任,以及经验的神话和对效果的迷信。因此,所有的诠释起步于怀疑,也要终结于怀疑,在所有人都被赋予怀疑权力的时代,抵御怀疑的唯一方案就是行动及其经验的结果。然而,诠释的最后波澜就消失在行动开始处。省察与诠释总是尝试让有序与无序融合在一个新的秩序结构之中,这种尝试一直是未完成的,行动对秩序的拆解与诠释对秩序的重构根本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面相而已。
不妨说,在被日常性统摄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是埋首于其中的,并且活在一个关于秩序感的迷信之中。与之相对,那种超然其外的病理诠释和秩序重构总是在日常断裂处才出现的。
被无限放大了的疫病隐喻和百无聊赖之中对日常的省察,让我们看到,某种秩序变成日常的基础就是其中必然包含着面向未来的“混乱”可能性,日常的截断和裂缝是必然,而不是某种偶然。善于反思且具有无穷想象力的我们既不是活在理性与秩序的清朗之中,也不是在无序与混乱的永夜之内,而是在清朗与晦暗的交界处,让黄昏永续。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疫情下的省思 | 程乐松:黄昏永续——“虚假观察者”关于疫病的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