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庆·综述】周五哲坛——Prof.Steven Crowell: Normativity, Reason and Phenomenology
本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主办的“周五哲坛”系列讲座邀请了来自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Steven Crowell教授担任主讲人。该系列讲座以“Normativity, Reason and Phenomenology”为话题,共分四次进行,题目分别为“Commitment: What is Self-Binding, and How is it Possible”、“Why ask Why? Retrieving Reason in Being and Time”、“Second-Person Reasons: Darwall, Levinas,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Reason”和“Horizons of Phenomenology: Metaphysics”;受篇幅限制,该系列讲座将分四次进行回顾。
Lecture 1.
Commitment: What is Self-Binding, and How is it Possible
2022年10月5日早上9点,第一场讲座在外哲所227室开讲。在讲座开始前,刘哲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题,并对参与会议的师生表达了欢迎与感谢。

讲座伊始,Crowell教授指出:“自我约束”(self-binding)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下,这种能力可以被称为“承诺”(commitment)或“决心”(resoluteness)。然而,对于这种能力的刻画存在一些悖论:John Haugeland认为,在这样的能力的驱使下,我可以主动地接受我要为之负责的对象向我展现出的那种生活、从而完成自我约束;但另一方面,这种约束的规范性来源似乎又只能是承诺自身——在Joseph Rouse看来,这令承诺所具有的“权威性”看起来仅仅是一个假象。Crowell则教授认为,这里实际上并不存在悖论,约束的规范性来源并不在具体物的秩序之中,而就在它们自身的存在(being)之中。
为了完成这一论证,Crowell教授首先分析了“被约束”(being bound)的特征——“被约束”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在的、是对于本身已经是一个统一体的现象的刻画(譬如,海德格尔所说的“Being-in-the-world”),另一种则是外在的、是对于并未形成统一体、但二者难以被分离的事物的刻画(譬如,被捆绑的人)。Crowell教授指出,触及“自由”本身的约束与情感层面的约束、文化层面的约束、以及“自然法则”的约束都不能等同——它是规范性的,即便我们有时在行动上看似可以“打破”它,也依然不能逃离它的约束。正如康德所言,“自由选择”并非“任性”(Willkür),它必然要以普遍法则(即,定言律令)的约束为基础,否则就会沦为欲望、自爱等偶然因素影响之下的非自由行动;在康德看来,“自主性”(autonomy)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约束,因为它将人类本性中的二重性(动物性和理性)统一成了一个整体。

根据康德的理论,“出于义务而行动”显然是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但是,我们是否有义务关注并建立自我的整体性?康德主义传统并没有对此给出答案,而海德格尔则给出了一个替代方案:“自我约束”源于此在的“操心”(care)——这样的结构中并不存在“理性”和“自由”这两者的相互关联。基于此,Christine Korsgaard提出:以实践认同(即,关于确认自我价值的描述)为基础的操心必然要求一个作为统一整体的自我,因为正是实践认同提供了我们行动的理由;而实践认同本身是以对自身作为“人类”的认同为基础的——这种意义上的自我约束是必然的,并且也是实践上可能的。
与Korsgaard不同,Stephen Darwall给出了另一种对于自主性的刻画。他认为,规范性的约束仅仅在我们能够占有“第二人称立场”(second-person standpoint)时才是可能的,而第二人称立场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人类作为实践性的主体,必然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而社会化的过程意味着我们不能独立自足地存在,而必然一直处在与他人的交互过程之中。Darwall认为,只有我们同时将自己视作“言说者”(addressor)和“收信者”(addressee)时,自我约束才具有权威性。
Crowell教授认为,Korsgaard和Darwall的立场实际上都与海德格尔对于义务的现象学描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Darwall对自我约束的考察并不局限于第一人称视角,而是从第二人称出发,取消了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我约束可能导致的悖论。test;

然而,对于自我约束的考察并未到此结束。Crowell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要规避人类本性中的“动物性”对自由带来的威胁,我们就必须将自由理解为我们本质的一部分,并且证明它寓于我们行动的每一个维度;在这种意义上,刻画“自我约束”的特征就是揭示我们存在的意义。如海德格尔所言,正是我们特殊的存在论和生存论性质为我们敞开了拥有自我约束特征的可能性:对于我们而言,存在本身成为一个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超越自身而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反思、因而拥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而这样的超越性就意味着自由。
虽然海德格尔并未对自由和自我约束的关联进行直接的刻画,但通过《存在与时间》,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对于日常性(everydayness)的描述中对此略知一二:当我们使用工具的时候,这些工具对我们而言或许合适、或许不合适,而“合适”或“不合适”的状态实际上就向我们揭示了一种规范性,即,它们应当是怎样的。由此可见,在与周遭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总会接触到一系列的规范性约束;而在出于实践认同而作出的行止(comportment)之中,我们的自由得以被揭示——这样的行动并不出于它所指向的、在它之外的目的,而是出于我们对自身的存在境况的领会与“操心”:我们对自己的存在方式有某种承诺,这样的存在方式向我们敞开一个特殊的、具有整体性的意义世界,我们在此之中以特定的方式与世界中的其它存在互动、受到这个世界的约束,并要为自己这样的存在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意义世界负责。


进一步地,Crowell教授表示,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对于实践认同的承诺,那么我们就会进入“畏”(Angst)的状态——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死亡”,即,无法成为任何存在者的状态。但对于我们——以“操心”为基本结构的存在者——而言,通过“良知”(conscience),我们得以理解自身作为这样的存在者所独有的现实处境以及自我约束所具有的无条件性: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我约束具有本体论上的必然性,这种意义下的自由意味着一种责任,它并不先于我们的存在,但同时无法被我们抛却;我们可以选择的只有自我约束的具体方式(本真的或非本真的)。这样一来,Rouse所提出的悖论便得到了回应——毕竟,约束的规范性就在于我们自身的存在之中。
在提问环节中,Crowell教授围绕“第二人称与第一人称立场的区别”、“在道德上具有负面意义的角色是否与正面的道德角色同样拥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康德与海德格尔对于自由问题的立场的区别”、“‘规范性’与‘道德’概念的关联”等问题,与刘哲老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Lecture 2.
Why ask Why? Retrieving Reason in Being and Time
2022年10月7日早上9点,第二场讲座在外哲所227室开讲。本场讲座接续上一场讲座的主题,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讨论的“操心”(care)、“良知”(conscience)等概念出发,考察早期海德格尔对于“理性”的理解。
在讲座的开始,Crowell教授重申了“操心”概念的特殊性:它并不是针对特定对象的特殊情感或态度,而是此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结构;海德格尔由此拒斥了哲学传统上对于“人”的定义,也拒斥了“理性”在人的本体论建构中的特殊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的理论最终会走向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相反,通过对“操心”的讨论,海德格尔将理性视为“操心”这一基本结构下的必然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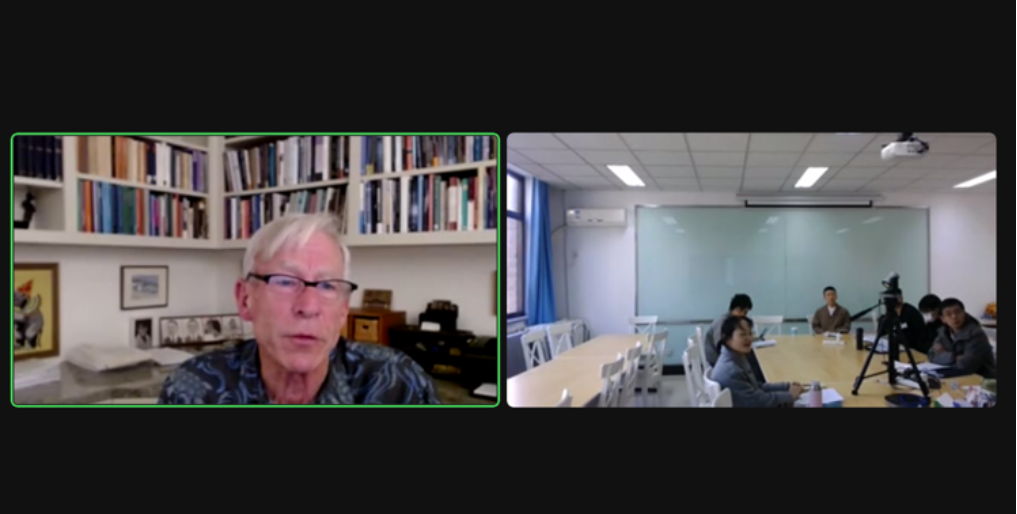
海德格尔将我们对存在者的认知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知觉或直观(nous,他常常将其翻译为perception 或intuition),另一类是通过逻辑(logos)。海德格尔在此跟随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认为通过前者,我们可以直接把握对象所显现出的“真”;同时,他将康德所言的思维的两个基本来源——感性(sensibility)和知性(understanding)——通过“想象的领会”(interpretation of imagination)联结成一个整体,并通过对行止(comportment)的现象学分析,尝试以“pure sensible reason”的道路来对“理性”进行解读。
海德格尔指出,康德认为经验科学要以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的能力为基础,而这两种能力使得作为整体的pure sensible reason成为可能;换言之,器物层面的超越性(ontic transcendence)要预设本体论层面的超越性(ontological transcendence, i.e. Heidegger’s term for Kantian “synthesis”),即,对于对象的存在本身的一种筹划(projection)。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样的超越性之中蕴含着“操心”这一基本结构,而这一结构意味着实践性自我的在先性。
结合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探讨,海德格尔指出,康德所言的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respect)正是对于实践性自我之存在的感受,而对于道德法则的把握必须要以对规范性本身的接受及对自身理性之自由特征的把握为前提。但是,与康德不同,海德格尔并不认为我们的理性先天地能够清晰把握自身的存在;以“操心”为基本结构的存在者包含一种“被抛”的指向,操心因而是此在的整体性结构的体现——它表明,对于此在而言,存在是一种“任务”,此在不得不进入到“去存在”(Zu-sein)的结构之中。而如果要把握自身的存在,那么此在就需要对于良知、对于此在的界限(即,“死亡”)拥有存在论意义上的领会——为此,我们需要对于此在的行止作进一步的考察。

Crowell教授指出,行止具有器物层面的超越性。在《存在与时间》第一部中,海德格尔集中讨论了我们如何与作为实践对象的器物打交道——正如上一次讲座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器物不是一系列性质的集合,而是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整体;并且,这样的意义整体需要在实践中显现,而不能仅仅通过占有它的概念来完成,也就是说,“意义”(meaning)实际上是前概念的(pre-conceptual),它依赖于直观而非逻辑。在行止的过程中,此在以特定的有意义的方式将其自身“视作”尝试以某种方式存在的状态,这包含着对自身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性(即,“能在”)的理解。由此可见,一切对于存在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在世存在的自我理解)都与此在的行止密不可分,行止因此具有器物层面的超越性: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作为“我筹划”(I project),总是要伴随“我”出于实践认同而作出的行动。
此外,行止也同样具有本体论层面的超越性——当此在的日常行止出现崩解时,本体论层面的超越性(亦即事实性特征和存在论特征的整体)就显现出来。日常行止的崩解意味着此在进入了畏(Angst)的状态中,在此状态下,此在会发现世界不再能给他自己提供任何有关实践认同的说明、任何事情都变得“不再重要”,他不再是在世界中的任何一类特定的存在者,一切行止都由此成为了“向死而生”(即,指向自身的界限)的筹划。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良知”能将作为实践主体的此在及其本真存在联结起来,这样的“良知”先于一切道德判断或应然法则——由此,作为logos的理性和作为nous的理性实际上是一体的——“理性”的各部分之间并不存在断裂。
进一步地,Crowell教授认为,虽然海德格尔在讨论“良知”时并未直接提及“理性”的概念本身,但他在论及对于良知的呼唤的回应时已经预设了此在对于理性所负有的责任,也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立法将理性的给予和操心的结构联结起来——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而非其他的方式、以此回应良知的呼唤,这正是理性的自我决定——也就是自由——的体现。

在提问环节中,Crowell教授围绕“实践活动是否预设了我们拥有最小程度的对于概念的理解”、“法兰克福式的‘瘾君子’是否同样受到规范性力量的作用”、“海德格尔和康德对于实践法则的理解是否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理性’的结构的观点有何区别”等问题,与刘哲老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展开了讨论。
提问结束后,刘哲教授对本次系列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向主讲人以及线上线下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感谢,并宣布本周讲座到此圆满结束。
Lecture 3.
Second-Person Reasons:
Darwall, Levinas,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Reason
2022年10月12日早上9点,第三场讲座在外哲所227室开讲。本次讲座以“第二人称理性”(second-person reason)为主题,聚焦第二人称立场下的态度、情感等问题,并对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
在讲座的开始,Crowell教授引述了Stephen Darwall的观点:“‘第二人称理性’一般被视为我们对于他人的指令与意志的规范性陈述。”不过,这不意味着一切指令都具有规范性;使得一个指令能够成为规范性陈述的关键要素在于,它所提供的行动理由是与主体相关联的,而指令的发出者对于接受者有某种意义上的权威性(authority)。那么,这样的权威性从何而来呢?Darwall的对此的回答是:这种权威性必须以双方具有同样的作为理性主体的能力和责任为基础;即便是不对称的权威关系,也要以这种对称的权威关系为基础。Crowell教授认为,Darwall的讨论是对于列维纳斯围绕非对称的规范性指令展开的现象学讨论的延续。
为了说明这一点,Crowell教授对Darwall的理论展开了分析——和Habermas一样,Darwall借助了Strawson的“反应态度”(reactive attitude)概念来说明第二人称立场所展现出的交互活动中的表述态度(performative attitude):它是对于“我”的表述性特征的一种体现,并且排除了中立的、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在此意义上,第二人称立场具有整体性,它是使主体有能力进入交互活动的前提;而第二人称立场本身则预设了“自主性”(autonomy)的能力,它要求主体能够预先从一个自由的理性存在者的立场出发,对自身进行规范性的约束——只有有能力约束自身,约束他人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这种对于第二人称立场的讨论实际上排除了人与上帝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对称的权威关系。

Crowell教授指出,Darwall的上述讨论涉及到了两个层面:一是对于交互活动中的表述态度的前提分析,二是对此类活动的边界的确立。然而,Darwall在此的分析可能涉及两点问题:第一,对于表述态度的前提分析中缺乏对于理性基础的说明;第二,在确立活动边界时缺乏对活动内部的必然性要求的刻画。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心理学事实,即,不存在明显的拒斥第二人称视角的途径。对于道德实践的讨论可以从发展心理学和道德启蒙的历史角度来入手,也可以从现象学的路径入手;Darwall和Habermas选择了前一种,而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则选择了后一种。Crowell教授认为,当Darwall尝试引入对于义务(obligation)的现象学讨论时,他没能很好地完成对于非对称关系的刻画;而列维纳斯的相关讨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第二人称立场的前提。
具体而言,Darwall认为,主体是在第二人称的实践当中被建构起来的,而这些相关的经验总是和指向他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然而,这样的论证预设了自我与他人在此类实践中的对称性,却并未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与Darwall不同,列维纳斯的“道德现象学”认为指令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存在原初意义上的不对称性:指令自身包含着对于指令接受者的限制,而这是接受者所不可逾越的;同时,指令的发出者相对于接受者而言具有优先性,这也是一种不可翻转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接收指令的经验就是一种对于已经占有的自由受到限制的经验;而对于“作为独立自然物进行任意的行为”的自由的限制,便会带来一种义务感——它规定了道德上的不可能性,并对我们施加了规范性约束:即便在实际行动上违反这样的指令,我们也依然无法脱离它——这正是我们进入规范性领域的最初原因。

那么,我们是如何知晓他人在第二人称的实践中所具有的权威性的呢?针对这一问题,列维纳斯引入了“欲求”(desire)概念——需要注意的是,“欲求”在这里特指我们对于善好的觉知、是一种包含对规范性指令的理解的反应态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对于能够满足各类日常需求的事物的正面态度。规范性的力量唤起了我们对于善好的欲求,而这种欲求推动了我们对于他者的“欢迎”——我们会倾向于进入与他人的交互活动之中,语言正是这样一种原初的给予,通过它,我们得以构建一个“共同的世界”。由此可见,对于列维纳斯而言,第二人称的立场,即,作为自由的理性存在者的对称性关系,是建立在对于他者的“欢迎”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并不包含对于理性的原始的偏好——恰恰相反,第二人称理性的形成是建立在第二人称立场的基础上的。
然而,列维纳斯在“谁是最初给出指令的‘他者’”这一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他将“指令者”的概念与神学概念区分开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的神秘性。Crowell教授指出,这样一种结构的关键在于:如果他者在我的良知(conscience)之外,那么他就无法向我显现他自身。在这里,“良知”正是像萨特意义上的“羞耻”(shame)那样的前反思的声明,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理想的规范性维度,即,展现“事情应当是怎样的”,而这被认为是理性的源头之所在。这与Darwall对于类似情感的理解颇为不同:心理学对羞耻的情感的描述是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它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应态度。Crowell教授认为,如果Darwall对于第二人称理性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列维纳斯就必须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在与他人的原初的不对称关系之上建立对称的权威性;但无论如何,列维纳斯的讨论给我们的提醒都是不可忽视的:道德空间的构建永远不会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游戏。

在提问环节中,Crowell教授围绕“第二人称视角与第一人称视角是否有本质区别”、“如果‘我’和‘他人’在规范结构中的位置是可交换的,那么‘我’与‘他人’的区别是什么”、“规范性关系是否包含某种特定的道德情感”、“海德格尔的‘良知’概念与列维纳斯的‘良知’概念有何区别”等问题,与刘哲老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展开了讨论。
提问结束后,刘哲教授对本次系列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向主讲人以及线上线下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感谢,并宣布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Lecture 4.
Horizons of Phenomenology: Metaphysics
2022年10月14日早上9点,第四场讲座在外哲所227室开讲。本次讲座以“现象学的边界”为主题,结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相关文本,探讨现象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象学的先验还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是否要求物理世界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依赖于意识”的问题。
在讲座的开始,Crowell教授对现象学与当代哲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现象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关注有着规范性结构的意义,这与意识、存在、现象等话题密切相关;而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论,现象学也对意向性关系和经验的结构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逻辑学类似,现象学并不必然被局限于“先验哲学”的领域,但它必然包含着规范性的维度:现象学对于具身化(embodiment)和时间性(temporality)的反思直接影响到认知科学的研究,对于同理心(empathy)和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研究对社会科学和人类学有着重要影响;而作为哲学的现象学,则应当被限制在胡塞尔意义上的“悬置”(epoché)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它并不能从其他科学那里获取任何前提。

基于此,Crowell教授提出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先验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密不可分?在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刻画时,胡塞尔如何理解“形而上学”?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Crowell教授首先对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概念进行了刻画:胡塞尔认为,自我只能在意向性活动流当中具体地存在,而这个过程同样也蕴含着对对象意义的建构;也就是说,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意识——事物在经验中的显现是一切认知和实践活动的基础,而这种显现本身实际上是“被悬置”的。在此意义上,先验还原就意味着对意识活动(conscious acts)及其意向对象(intentional objects)和形成意义的综合活动(the syntheses of identification)之间的互动结构进行反思,而这应该以一种“形而上学中立”的方式被理解——它不要求任何对于自然态度下的对象作出本体论承诺,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它们作为“意义统一体”(unities of meaning)所展现出的知识论特征;在此过程中,意识自身的存在总是预先被给予的。由此可见,现象学仅仅是对于意义和为真性的先验澄清,而不涉及对事物自然本性的考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胡塞尔的部分文本本身具有模糊性,对于“实在性形而上学地依赖于意识”这一立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澄清。为此,Crowell教授介绍了三位当代学者围绕此话题展开的讨论:

1. Rudolf Bernet
Bernet认为,胡塞尔的唯心论是形而上学中立的,因为它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唯心论,关注知识活动和知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区分“依赖于意识之物”和“独立于意识之物”没有意义,毕竟意识所能构建起的“实在世界”必然是经验活动及其对象互动的结果。Bernet对于宽泛意义上的唯心论和严格意义上的唯心论作了区分:前者有关对象的可能性和对于这些对象的直观的可能性的必然联系,后者则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与世界的事实性(facticity)相关,认为事实的存在有赖于具身化主体的事实存在——Bernet指出,我们很难从先验现象学当中找到后者存在的证据。
2. Dan Zahavi
与Bernet相似,Zahavi也认为先验主体性并非笛卡尔意义上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的意识,并同意先验唯心论不是某一特定类型的“形而上学唯心论”,而是以理解“对象性”的意义为目的。但是,与Bernet不同的是,Zahavi认为先验唯心论暗示了反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立场;他指出,在现象学的立场之下,对于世界在本体论层面的“客观的”理解是必须被拒斥的。此外,如胡塞尔所言,“如果没有拥有认识对象现实性的现实主体,那么对象就不可能被把握为现实的”——这也同样包含了对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不对称关系的刻画。先验现象学由此有意地模糊了本体论和知识论之间的界限,因为在此意义上,存在、实存、现实性等概念的定义都是由它们的意义被给予和被建构的过程所决定的。
3. Ullrich Melle
Melle对于胡塞尔的文本重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指出,胡塞尔的论证关注的核心之一在于:知觉在被引向实在事物的同时,也在判断活动的过程中被直接引向了对于实在事物的认识的为真性。这的确意味着本体论和知识论的界限的模糊——“世界不可能脱离自我对其的把握而存在”,因为有关独立于意识的世界的任何陈述的为真性都不可能得到证明。Crowell教授指出,Melle和Bernet与Zahavi一样,都要求意识首先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并通过意向性活动实现它自身的意识,这必然是一种具身化的、具有交互主体性的意识;但是在Melle看来,胡塞尔从这一点出发,将论证引向了形而上学唯心论的结论。
在讲座的最后,Crowell教授对于上述讨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这些讨论要求我们对于两种基本的形而上学立场——先验论和自然主义——进行反思,同时也提醒我们:先验现象学实际上可以并且应当保持形而上学中立,它应当为科学和神学的相关讨论留出空间。

在提问环节中,Crowell教授围绕“如何理解‘形而上学中立’和‘形而上学依赖’”、“是否所有有关反思的明见性都是绝对的”、“胡塞尔在何种意义上认为意识是一种‘单子的统一体’”等问题,与刘哲老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展开了讨论。
提问结束后,刘哲教授对本次系列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向主讲人以及线上线下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感谢,并宣布本次系列讲座到此圆满结束。



